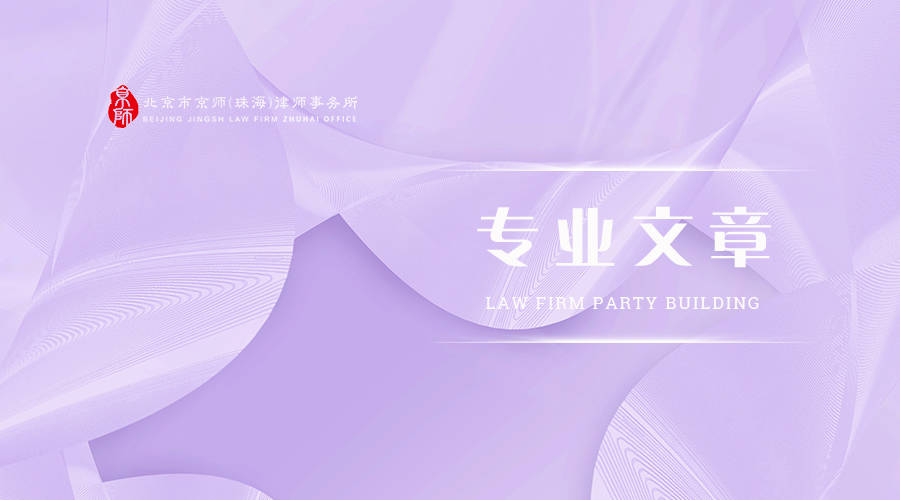
01问题的提出
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权利人往往通过授权方式将维权权利转让给第三方公司,由其代为提起诉讼。然而,若被授权方仅获得诉讼维权的权利,而未实际取得著作权的实体权利,其是否具备适格的原告资格?本文结合典型案例(2021)粤73民终3270号及《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分析司法实践对“维权权利单独转让”的效力认定,并探讨此类授权的法律风险及实务建议。
02典型案例
(2021)粤73民终3270号案件,长沙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与广州某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是典型的仅授权维权权利的案例。
经法院审理认为:长沙公司虽与著作权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许可使用协议》,但其明确表示授权目的仅为“帮助作者维权诉讼,并就侵权索赔进行利益分成”,并未实际使用作品或支付许可费用。最终法院最终认定长沙公司未取得实体权利,仅受让了程序性诉权,故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03法律分析与司法实践趋势
(一)法律分析
1.程序权利脱离实体权利单独转让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起诉必须符合“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条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及意味着著作权维权诉权必须依附于实体权利(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等),不得单独转让,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适格原告应当是著作权人或者依法取得著作权相关权利的主体。
案例中,长沙公司虽与著作权人签订了独占性许可协议,但其真实意图并非实际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通过诉讼维权获利。因此,该授权行为实质上是将“诉讼权利”单独转让,而并未真正转移著作权的实体权利。,故此长沙公司未获得实体权利,仅受让程序性诉权,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2.著作权立法目的的限制
根据《著作权法》第24条的规定,许可使用的核心在于“使用”,而非单纯维权,宗旨在于鼓励创作和促进作品的合法传播,而非单纯支持维权诉讼。若允许商业公司仅以维权为目的获取授权,可能导致“批量诉讼”现象泛滥,使司法资源过度消耗于商业性维权,而非真正的著作权保护。 如此弊端突出,过分强调商业利益则会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也必将偏离《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二)司法实践趋势
虽然前些年各地法院针对这种情况存在不同的判决,但近年来,司法实践对“仅授权维权权利”的原告资格问题逐渐形成统一观点:维权诉权不能单独转让,必须依附于实体权利。
04权利人的救济途径
尽管仅授权维权权利的原告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被驳回起诉,但对于真正的著作权人而言,其包括诉权在内的其他权利并未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和影响,仍可以通过如下方式维权:
1.自行起诉:著作权人自行进行维权诉讼;
2.实体性授权:将实体性权利与维权程序性权利一并实质授予的主体进行诉讼维权。
05结语
著作权维权授权的合法性边界,取决于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不可分性。司法实践通过否定“仅授权维权权利”的原告资格,维护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与诉讼制度的严肃性。
知识产权保护本着“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的精神,只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著作权人或者所授权主体采取的维权方式都应当得到司法的认可,也鼓励广大权利人,积极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击“盗版”。

作者:罗秀梅律师,京师全国年度优秀律师,两江新区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京师(重庆)法律顾问及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十多年来专注企业法律服务,拥有多年大型集团企业法务负责人经历,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和知识产权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较强的“法商思维”能力,善于站在老板立场分析解决问题。曾发表《著作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侵害著作权案件的抗辩事由》《专利侵权案件中合法来源抗辩思路》等多篇专业文章。
执业领域: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

作者:张兴卫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执业于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拥有多年大型集团企业法律事务经验。对知识产权检索、申请等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参与多起知识产权诉讼,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商标无效、复审、侵权纠纷等知识产权案件有丰富的办理经验。曾发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比对探讨》《“商标异议”应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知识产权之专利权评价报告》《当娱乐遇上法律:观影录屏构成侵权否?》等多篇专业文章。
执业领域: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