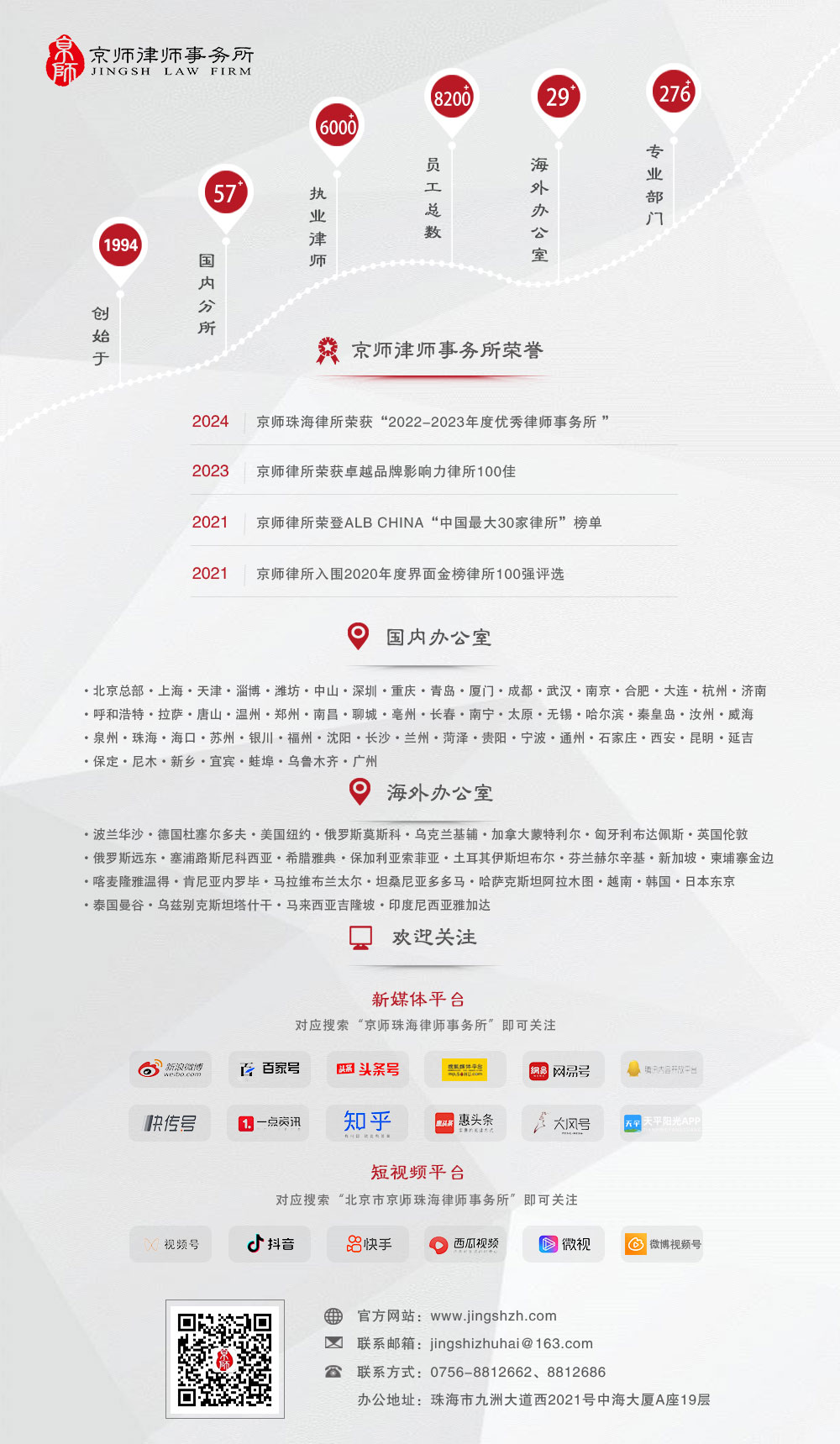►作者:锁贺律师
一、裁判要旨
在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显名纠纷中,需围绕“实质出资” 与“股东资格认可” 的核心要件,结合代持协议效力、其他股东态度、实际权利行使情况综合判定。我们处理此类案件时,应优先审查实际出资人是否满足法定显名条件(如合法代持关系、实际出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知情无异议),区分“明示同意”“默示认可”“名股实债” 等不同情形适用法律;对实际出资人主张显名的诉求,需平衡其权益与公司人合性、外部债权人信赖利益,同时明确显名失败后的权利救济路径,避免仅依据工商登记或代持协议外观机械裁判导致利益失衡。
二、案情简介
(一)当事人
1.上诉人(原审被告):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登记股东张某
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实际出资人李某
3.原审第三人:甲公司其他股东王某、赵某、孙某
(二)基本事实
2018年,李某因身份限制(规避公务员不得参与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规定),与张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李某向甲公司出资200万元,由张某代持该部分股权(占甲公司注册资本20%),李某享有投资收益及股东决策权,张某仅代为登记。
1.2018年至2022年,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向甲公司支付200万元,备注“投资款”,甲公司出具《出资确认函》;李某多次以“实际股东”身份参加甲公司股东会(有会议签到记录及决议签字),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如项目投资、高管任免),并按20%比例收取分红(有银行流水及甲公司财务凭证佐证)。
2.2023年,甲公司股权价值上涨,张某以“工商登记股东” 为由主张股东权利,拒绝配合李某显名;甲公司其他股东中,王某、赵某明确同意李某显名,孙某以“不知情” 为由反对,张某亦明确反对。
3.李某起诉请求:确认其为甲公司股东(持股20%),判令甲公司、张某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甲公司、张某反诉请求:确认《股权代持协议》因规避法律无效,李某无权主张股东身份。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代持协议》虽因规避公务员禁令存在效力瑕疵,但李某已实际出资且长期行使股东权利,其他股东过半数(王某、赵某)知情且无异议,符合显名条件,判决支持李某诉求。甲公司、张某不服上诉,主张“代持协议无效即丧失显名基础,且孙某反对导致未满足‘过半数同意’”。
三、裁判要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股权代持协议》效力是否影响显名、李某是否满足显名条件、甲公司及张某是否需协助办理变更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1.代持协议效力与显名的关联性:区分“协议效力” 与“显名条件”
根据《民法典》第153 条、《公司法解释三》第24 条第1 款,代持协议若因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不必然导致实际出资人丧失显名权利,需审查实际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及公司内部认可情况。本案中,李某规避公务员经营禁令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协议效力虽存在瑕疵,但:一是李某实际出资200万元已计入甲公司实收资本,出资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二是甲公司及其他股东长期认可李某的股东权利行使,形成稳定的内部法律关系;三是公务员身份限制不影响其事后通过合法程序(如离职后)主张显名,故协议效力瑕疵可通过补正消除,不阻碍显名审查。
2.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核心条件: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 条第3 款、《九民纪要》第28 条,显名需满足“实际出资+ 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知情无异议”。本案中:一是李某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出资确认函》、财务凭证,证明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二是李某提交股东会签到记录、决议签字、分红流水,证明其长期行使股东权利,王某、赵某作为其他股东知情且未提出异议,孙某虽当庭反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此前对李某的权利行使提出过异议,应认定“过半数其他股东知情无异议”;三是张某作为名义股东,以工商登记对抗实际权利,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故李某满足显名的法定条件。
3.工商变更登记的履行义务:公司及名义股东的配合责任
根据《公司法》第32 条第2 款、《公司法解释三》第23 条,实际出资人满足显名条件后,公司有义务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名义股东需予以协助。本案中,甲公司及张某以“孙某反对”“协议无效” 为由拒绝配合,缺乏法律依据:一是孙某的反对未形成于李某行使权利的合理期限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二是协议效力瑕疵已通过李某的实际出资及公司内部认可补正,故甲公司、张某需在判决生效后15 日内协助李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四、裁判规则深度解读
(一)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法定条件: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审查
1.基础要件:合法的出资与代持合意
(1)实际出资的认定标准:需提供“出资凭证+ 公司认可” 证据
一是资金性质明确:转账备注“投资款”“出资款”,或公司出具《出资确认函》《股权证》,会计账簿将款项计入“实收资本” 而非“其他应付款”(区分“出资” 与“借款”)。例如,在(2019)苏04 民终4344 号案中,沈某提供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证明出资,法院认定其满足出资要件;二是出资来源合法:排除违法资金(如赃款)或规避金融监管的资金(如违规私募),若出资来源违法,即使完成出资也无法显名。
(2)代持合意的证明要求:书面协议优先,无书面协议时结合履行推定
一是有书面协议的:需明确约定“实际出资+ 权利归属”,如《股权代持协议》中载明“李某享有股东权利,张某仅代为登记”;二是无书面协议的:可通过股东会决议、分红记录、经营参与凭证推定合意,例如,在(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213 号案中,蔡某某无书面代持协议,但结合出资收据、股东会签到记录,法院推定代持合意成立。
2.核心要件:其他股东的“同意” 或“知情无异议”
(1)“过半数同意” 的认定范围:仅计算“其他股东”,排除名义股东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 条第3 款,“其他股东” 指名义股东之外的公司股东,人数过半数即可,不要求股权比例过半数。例如,甲公司有股东张某(名义)、王某、赵某、孙某,李某显名时需王某、赵某、孙某中过半数(2 人)同意或知情无异议,张某的意见不纳入计算。
(2)“同意” 的表现形式:明示与默示均认可
明示同意:包括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李某显名”、股东出具《书面同意函》、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等。例如,在(2021)甘民终127 号案中,其他股东在股东会纪要中确认实际出资人持股比例,构成明示同意。
默示认可:实际出资人长期参与经营(如参加股东会、派驻高管、审批决策),其他股东在合理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例如,本案中李某连续5年行使股东权利,王某、赵某未提出异议,构成默示认可;而在(2019)最高法民申2884 号案中,虹联公司无法证明其他股东知情,故未获支持。
(二)特殊情形的裁判规则:风险与例外处理
1.代持协议无效时的显名路径
(1)协议无效但出资合法:可通过“公司内部合意” 补正显名
若代持协议因规避法律(如公务员代持)无效,但实际出资合法且公司内部认可,实际出资人可在消除效力瑕疵后(如公务员离职),凭实际出资及权利行使证据主张显名。例如,本案中李某若离职后主张显名,协议效力瑕疵消除,可直接依据内部认可显名。
(2)协议无效且出资违法:丧失显名权利,出资按“不当得利” 返还
若出资来源违法(如用非法集资款出资),或出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如代持上市公司股权规避监管),实际出资人不仅无法显名,还需返还出资(扣除公司损失后)。例如,在(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案中,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因损害公共利益无效,实际出资人无法显名,出资按不当得利返还。
2.“名股实债” 与显名的区分
(1)“名股实债” 的认定特征:无股东权利行使,仅追求固定收益
若实际出资人约定“固定回报+ 到期回购”,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即使登记为股东,也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无权显名。例如,在(2016)最高法民再307 号案中,海天公司仅收取固定收益,不参与经营,法院认定为“名股实债”,驳回显名请求。
(2)与股权代持的核心区别:是否具备“股东权利行使” 的实质
股权代持中,实际出资人会实际参与经营、承担风险(如亏损时按比例承担责任);“名股实债” 中,实际出资人仅关注资金回收及固定收益,不介入公司治理。例如,本案中李某参与股东会决策、承担经营风险(如项目亏损时按比例承担损失),属于股权代持,而非“名股实债”。
3.外部债权人介入时的显名限制
(1)内部显名与外部债权的冲突:优先保护善意债权人
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若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代持股权,实际出资人即使满足显名条件,也无法对抗善意债权人,仅能向名义股东主张赔偿。例如,在(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案中,实际出资人因无法对抗债权人的强制执行,显名请求被驳回。
(2)非善意债权人的例外:可通过证明债权人知情排除执行
若实际出资人能证明债权人明知代持关系(如债权人与名义股东恶意串通),则债权人不构成“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可排除强制执行并主张显名。例如,在(2020)最高法民申964号案中,实际出资人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知晓代持,法院支持其排除执行及显名请求。
(三)显名失败后的权利救济:路径与范围
1.向名义股东主张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 条第2款,若名义股东违反代持协议(如拒绝配合显名、擅自处分股权),实际出资人可主张赔偿损失,损失范围包括股权价值增值部分、预期分红等。例如,在(2018)鄂07民终458号案中,名义股东拒绝配合显名,法院判决其赔偿实际出资人股权增值损失500 万元。
2.向公司主张出资返还(限于特定情形)
(1)增资未完成且目的落空:若实际出资后公司未办理增资登记,且无法达成显名合意,可要求返还出资。例如,在(2018)吉0112民初2031号案中,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实际出资人主张返还出资,法院予以支持。
(2)公司恶意阻碍显名:若公司故意不召开股东会、隐瞒其他股东意见,导致显名无法实现,实际出资人可主张解除出资关系并返还出资。例如,在澳仪公司与唐颖纠纷案中,公司拒不配合显名,法院判决返还出资17 万元。
3.举证责任分配:实际出资人的核心举证义务
(1)证明实际出资:需提供转账记录、出资确认函、财务凭证等,若仅提供收据无转账记录,可能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2)证明权利行使:需提供股东会记录、决议签字、分红流水、经营决策文件等,无证据证明权利行使的,难以认定“其他股东知情无异议”;
(3)证明代持合意:无书面协议时,需通过多份证据形成完整链条,例如,出资凭证+ 分红记录+ 其他股东证言,单独证据难以推定合意。
五、实务经验总结
(一)实际出资人的风险防控
1.签订规范的《股权代持协议》:明确约定“实际出资范围、股东权利行使方式、显名条件、违约责任”,避免模糊表述;若存在身份限制(如公务员),可约定“身份限制消除后协助显名”,降低协议无效风险。
2.留存出资与权利行使证据:包括银行转账备注“出资款”、公司出具的《出资确认函》《股权证》、股东会签到记录、决议签字页、分红流水、经营决策邮件等,形成完整证据链。
3.提前获得其他股东认可:显名前通过股东会决议、书面确认函等形式,固定其他股东的同意意见;若无法获取明示同意,需确保长期、公开行使股东权利,留存其他股东无异议的证据(如会议录音、聊天记录)。
4.关注名义股东信用状况:选择信用良好、无大额债务的名义股东,避免因名义股东被强制执行导致股权被查封;可约定“名义股东对外担保需经实际出资人同意”,防范股权处分风险。
(二)公司及其他股东的风险防控
1.完善股东资格审查机制:接受出资时,核实实际出资人身份,避免因代持协议无效导致纠纷;对代持情况进行内部登记,留存《股权代持协议》复印件,便于后续显名审查。
2.规范股东会决策程序:涉及实际出资人权利行使的事项,需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其身份,由其他股东签字确认;若对实际出资人身份有异议,应及时提出并留存书面异议记录,避免事后被认定为“默示认可”。
3.平衡人合性与实际权利:若其他股东反对实际出资人显名,需提供合理理由(如实际出资人损害公司利益、缺乏合作基础),避免仅以“工商登记” 为由拒绝,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可通过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行使等方式,化解人合性冲突。
(三)名义股东的风险防控
1.明确代持权利义务边界:在《股权代持协议》中约定“不承担经营风险、不享有投资收益”,避免因公司亏损被要求承担责任;约定“实际出资人行使权利需书面授权”,防范越权行权导致的赔偿风险。
2.留存实际出资证据:保留实际出资人转账记录、出资确认函等,证明自身仅为代持,避免被认定为实际股东;若实际出资人未按约定出资,及时书面催告并留存证据,防范出资不足的连带责任。
3.及时配合显名或解除代持:实际出资人满足显名条件时,应按协议配合办理变更登记,避免因违约承担赔偿责任;若不愿继续代持,可书面通知实际出资人解除协议,要求其限期显名或转让股权。
六、延伸裁判阅读
裁判规则一:未参与经营的实际出资人,因举证不足无法显名
案例:(2019)最高法民申2884 号(虹联公司与安捷医院股东资格确认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虹联公司主张其为安捷医院实际出资人,但:一是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唐某某、马某某)知情;二是无证据证明其参与经营、行使股东权利;三是提交的会议纪要无其他股东签字,出资证明书真实性存疑。故虹联公司未满足“其他股东过半数知情无异议”,驳回其显名请求。
裁判规则二:代持协议无效但出资合法,补正后可显名
案例:(2021)甘民终127 号(吕某某与某投资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吕某某与赵某某的代持协议因规避股东人数限制存在瑕疵,但吕某某已实际出资且公司其他股东长期知情,吕某某离职后消除身份限制,补正了协议效力瑕疵,故支持其显名请求,判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裁判规则三:“名股实债” 中,实际出资人无权主张显名
案例:(2016)最高法民再307 号(海天公司与太和公司出资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海天公司向太和公司出资时约定“固定年利率12%+3 年后回购”,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虽备注“投资款”,但符合“名股实债” 特征,故海天公司无权主张显名,仅能要求返还本金及利息。
裁判规则四:其他股东事后反对,不影响“默示认可” 的认定
案例:(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213 号(蔡某某与消防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蔡某某长期参与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消防公司及其他股东(含登记股东蓝某某)此前未提出异议,诉讼中突然反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认定“其他股东已默示认可”,支持蔡某某显名请求。
律师简介

锁贺 律师
联系方式:17612123366
执业近七年,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上市公司董秘资格,凭借专业的法律技能与敏锐的商业思维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取得了稳定的合作。
承办的系列建工类、公司类疑难商事案件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处理企业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法律服务、各类投资合同引发的诉讼或非诉事宜中,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