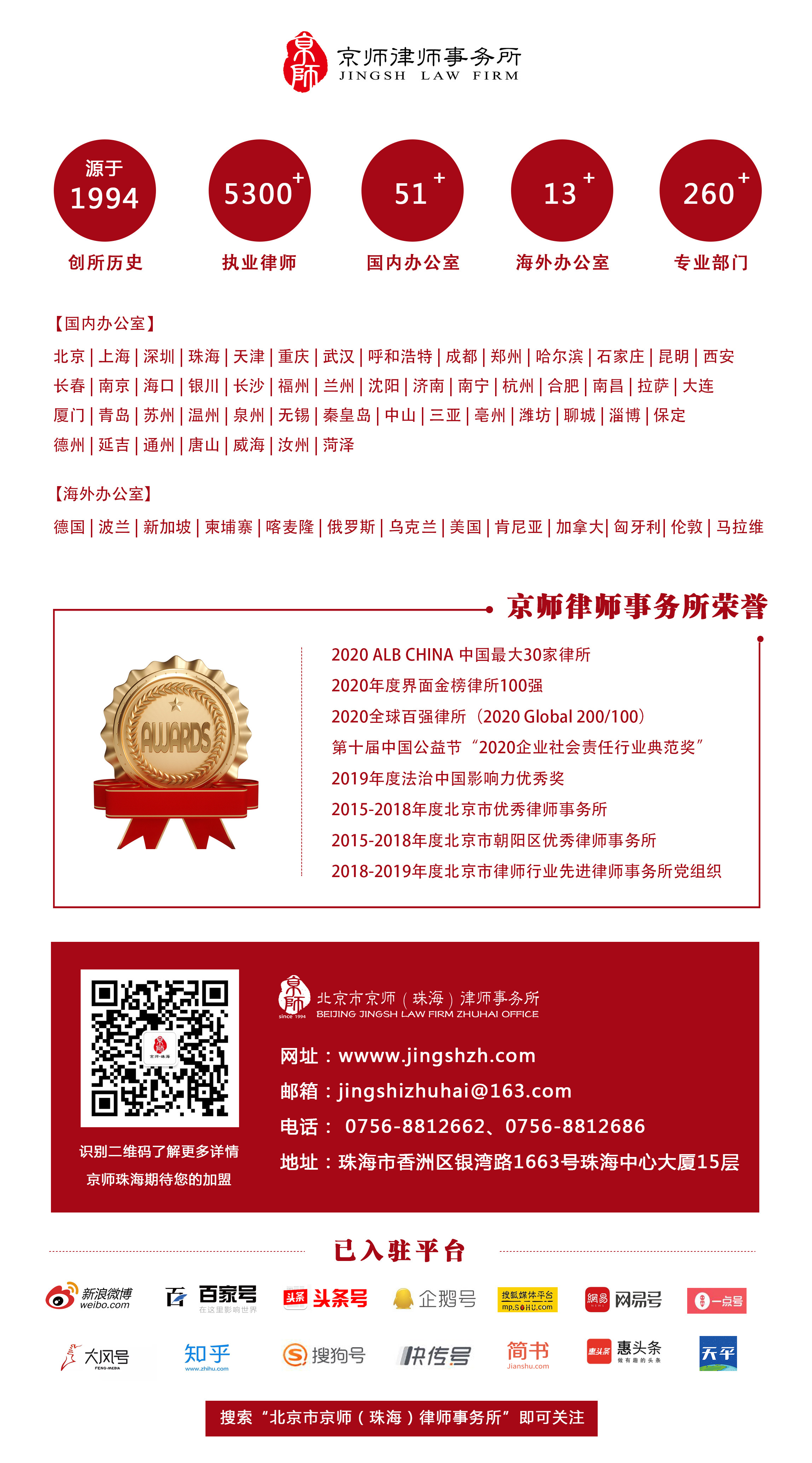苦寻14年后,12月6日中午,电影《亲爱的》的原型孙海洋终于见到了失而复得的儿子孙卓。视频里,他紧紧抱住儿子,久久不肯放开,失声痛哭。
虽然孙卓已经找寻到了亲生父母,但由于他从幼时就与原生家庭分离十四年,他是否能够适应或恢复和亲生父母的关系?生父母与“养父母”的矛盾与纠纷又应该如何化解?
孙卓被拐时,岁数还很小,他与生父母之间并无实质上的情感。十多年后,生父母的突然出现,对他来说,在短时间内仍是生活中的陌生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生父母历尽艰难寻回的子女,他们肯定会被当作亲人看待,这两种感情上的天然落差必然会造成一系列家庭情感上的矛盾。
反观孙卓的“养父母”,他们将孩子抚养长大,一定投入了大量心血,虽然他们与孙卓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孩子的性格、生活习惯等已经与“养父母”融合。

▲孙海洋与儿子见面后抱在一起。来源:视频截图
在笔者办理与知悉的拐卖儿童犯罪中,被拐卖时十岁以下特别是五岁以下的儿童,被解救后愿意回到生父母身边的比例较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不愿意回到生父母身边的孩子,如果将他们强行与“养父母”分离,可能会给双方家庭造成困扰,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对于被生父母贩卖的儿童,再将其送回曾经伤害他的人身边,将会对于保护儿童权益更为不利。
如果“养父母”就是拐卖儿童的买方呢?他们又何尝不是伤害孩子的元凶之一?天下本无感同身受,不经历失子的切肤之痛,就不会懂得对买卖的刻骨之恨,更不能理解对帮凶的深恶痛绝!
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收买被拐卖儿童案件中的“养父母”应否构成犯罪?
据警方透露,拐卖孙卓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捕,帮助其藏匿孩子的同犯也正在申请批捕中。除正在生病的孙卓“养父”外,孙卓的“养母”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理中。
“买方入刑”的尴尬
我国早在1997 年的《刑法》中,就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做出规定,但也规定了对收买犯罪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较为猖獗,本条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刑罚的严厉性和威慑作用,削平了预防和惩治犯罪的效果,助长了收买人的嚣张气焰。
要知道,正是因为有大量的“收买”需求,才导致并推动了“拐卖”行为的高发,收买本来就是贩卖儿童交易链的一环,若对收买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将会促使部分家庭铤而走险,客观上致使拐卖犯罪屡禁不止。
正因为如此,在2015年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相关规定,其中最大的变革点是将上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修改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增加了对收买行为的处罚力度,从“没有购买就没有拐卖”的角度出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拐卖儿童行为的犯罪链条,也进一步加强了收买犯罪与拐卖犯罪的量刑贴合度,使得刑事处罚相互衔接、循序渐进,有章可循。
然而,事物总有两面,加重刑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社会秩序,强化了法律对被害儿童的保护力度,但是若将“收买”行为一律入刑,摈弃以往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客观上也使得收买家庭主动帮助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而且,从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只有在同时符合“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时,才可以从轻处罚。如果仅仅没有虐待行为,但是不愿意帮助被买儿童寻找亲生父母,或者采用搬家、为被买儿童隐匿姓名、为其另报户口进行“洗白”等方式逃避对被拐儿童解救的,是不能享受上述从轻处罚的量刑幅度。
这种在定罪量刑上的简单划分,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有些主观恶性不大,对被收养的孩子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与犯罪意图大,虐待被收养儿童的收买人无法在定罪量刑上做出有效地区分,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效果,不利于维护法律公平公正的实施。
不仅如此,由于被拐儿童的寻亲之路往往十分漫长,对跨越《刑法修正案(九)》的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应该如何处理?而且,因“新法”较“旧法”重,对于《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的收买行为、被害人尚未被解救的情形应当如何适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在本案中,孙卓“养父母”收养孙卓发生在2007年,《刑法修正案(九)》施行时间是2015年,孙卓“养父母”是否可以基于《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从而适用1997年《刑法》对该罪的较轻规定,进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仍然还有待于司法部门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断。

▲2012年2月,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举行解救被拐卖儿童认亲大会
“天下无拐”,不能只靠刑法
笔者认为,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刑法规制纵然重要,但犯罪的预防却不能仅靠《刑法》一家之功。
与其一味地加大对收买者的刑事惩戒,不如强化社会综合治理的成效,不仅要依法从打拐源头的“贩卖”与末端的“收买”抓起,同时还可以制定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相类似的罪名,把帮助提供诸如“出生证”“户籍证明”“结婚证”等用于为被拐卖儿童洗白证明的“帮凶”准确定罪,从而全方位地提高对拐卖儿童的惩戒力度。
众所周知,被拐儿童不具备上户口的条件,其能瞒天过海安然落户,必然存在着“出生证”等造假以及户籍部门渎职等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另一方面,由于收买犯罪的最高量刑只有三年,笔者呼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刑法》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罚,细化犯罪情形和量刑情节,扩大从重处罚与从轻处罚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区别对待“可以从轻处罚”的两个适用条件,根据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意图大小等给予不同的刑事规制手段,努力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目标。
对于存在对被拐儿童限制人身自由、虐待、性侵、出卖人体器官等违法犯罪情形的,或者强迫被收买儿童从事乞讨、苦役等行为的收买者,可以考虑通过数罪并罚等刑罚手段强化惩戒力度。对于收买遗弃、无力供养家庭的儿童或者对《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实施的收买行为,在收买后没有虐待的养父母,建议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原刑法的规定,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此外,还应从疏导需求的角度充分考虑部分不孕不育家庭、失独家庭收养子女的需求。目前,由于民事法律对收养子女的门槛和要求较高,加之收养程序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使得部分家庭“被迫”采用非法手段来满足自身的收养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拐卖儿童行为的发生,对此,我们有必要对配套的法律予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愿天下没有“失子之痛”,衷心期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快乐成长!

朱政律师
朱政,执业律师,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主任,国家高级经济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咨询专家,第八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破产与重整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安徽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纪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司法厅确定的安徽律师调解员,安徽省商会调解员,安徽省《民法典》讲师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