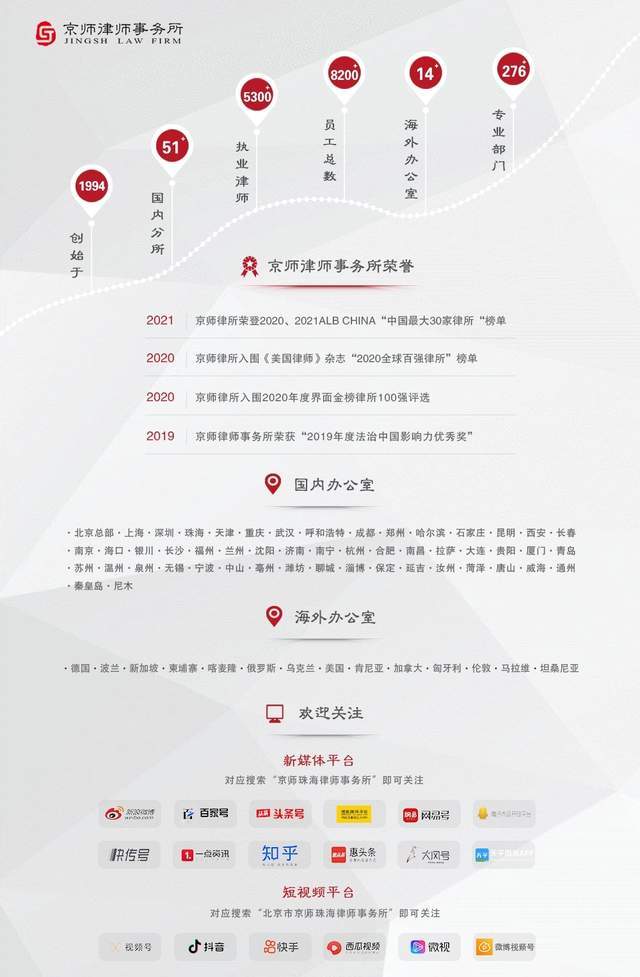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现结合本人参与代理的一起涉外刑诉案例讨论相关言词证据的合法性。
该案被害单位为一家外资企业,在追索欠款过程中被骗1.9亿人民币的诉讼保全保证金。在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过程中该单位大部分外籍高管自带翻译出具证人证言,个别高管直接用中文接受调查取证。针对此情况对方辩护律师申请将自带翻译出具的证人证言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根据为《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而不能自带翻译。毫无疑问,一旦这些证人证言被排除,对于被害单位来说将是灭顶之灾,排非申请当然也给侦查机关及公诉方带来了困扰。
从直觉上说,证人自带翻译接受侦查机关调查取证应当是没有问题,也符合正常的做法,证据排除应当是不成立的。带着这种信念本人对该部分证人证言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为公诉方提起公诉及法院判决提供了强力支持,促成了案件圆满结束。
《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权利与义务相辅相生,保障证人权利是相关机关翻译义务的基础,二者不可分割。参与人自带翻译,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体现了权利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免除了相关机关为其翻译的义务。只有因各种原因没有翻译时,侦查机关才有为其翻译的义务,具有最终保障的意义。外籍证人自带翻译或会讲中文情况下本身不存在语言沟通的问题,就不需要侦查机关再为其翻译。
公安机关在进行讯问、询问时首先向证人、被害人等出示全国通用的《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其第一项即为: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时有权要求配备翻译人员,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该项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第9条通俗化的理解或阐释。该项虽然没有明确是自己配备还是公诉机关配备,但理解成公诉机关配备更显示了其最终保障诉讼参与人用本民族证言进行诉讼权利的意义。“有权”则更体现出诉讼参与人对公诉机关配备翻译的选择性。也就是公诉机关配备翻译是保障而不是必须。当然,对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也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也可以放弃权利直接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外籍证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了最终保障,应由其本人提出,而不是由辩护人一方提出。本案当中是外籍高管被骗才致使被害单位蒙受损失,外籍高管既是证人也是被害人。基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而将被害人陈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是极其荒唐的。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辩护人提出排除证据适用法律只引用了《刑事诉讼法》第9条的后半段,回避了该条的前半段,即: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显然,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分才是该条规定的核心、根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提供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保障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很明显,辩护人是在依自己的意愿”创设“法律,为其证据排除提供所谓的法律依据。
所谓证据排除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无论如何理解也得不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中”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时有权要求配备翻译人员,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结论,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其根源在于其完全偏离了第9条规定的保障诉讼参与人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一核心和本质。前者更多体现的则是诉讼参与人必须接受公诉机关提供翻译的义务,而非权利。
辩护人所称外籍高管自带翻译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也是不能成立的。翻译的公正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漫无边际的。翻译的公正即是否表达了被翻译人的意思,或是否为被翻译人所认可。外籍人员自带翻译,首先是对翻译的认可,不存在公正问题。外籍证人作为被害单位的代言人或证人,其陈述的性质是控告,对被告人不利是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是翻译是否公正的问题。外籍证人证言是其对事件完全自主的单方陈述,找一个和被告人有仇的翻译来达到对被告人不利的效果是滑稽可笑的!辩护人对(可能)公正的质疑是毫无根据!
翻译的公正即是否表达了被翻译人的意思,或是否为被翻译人所认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关机关为多方或单方指定翻译时才存在翻译是否持公正立场及是否有翻译资质的问题,究其原因是他人为被翻译人指定翻译及被翻译人对翻译不了解。正是基于此,当事人可提出翻译回避的申请,避免翻译结果不能代表已方意思表示并强加于己方。外籍人员所自带翻译不为被告方提供任何翻译服务,不存在是否正确表达被告方意思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辩护人基于可能影响公正而申请证据排除更是完全没有道理!
通过论证分析,打消了公诉机关及法院对外籍人员证人证言合法性的顾虑,为公诉方提起公诉及法院判决提供了强力支持。通常情况下,法律规定首先应当是合理的,出现明显不合常理的情况往往是法律适用存在问题,比如该案当中的证据排非申请引用法律依据就是明显的主次不分,甚至以偏概全。
作者介绍

于银杰,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北京市京师(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深度参与矿产资源法及国务院相关领域系列行政法规修订工作。2015年至2018年期间直接支撑自然资源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现任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鄂尔多斯市国际商会矿业法律智库专家、北海仲裁委矿业仲裁员、京师律师事务所无罪辩护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