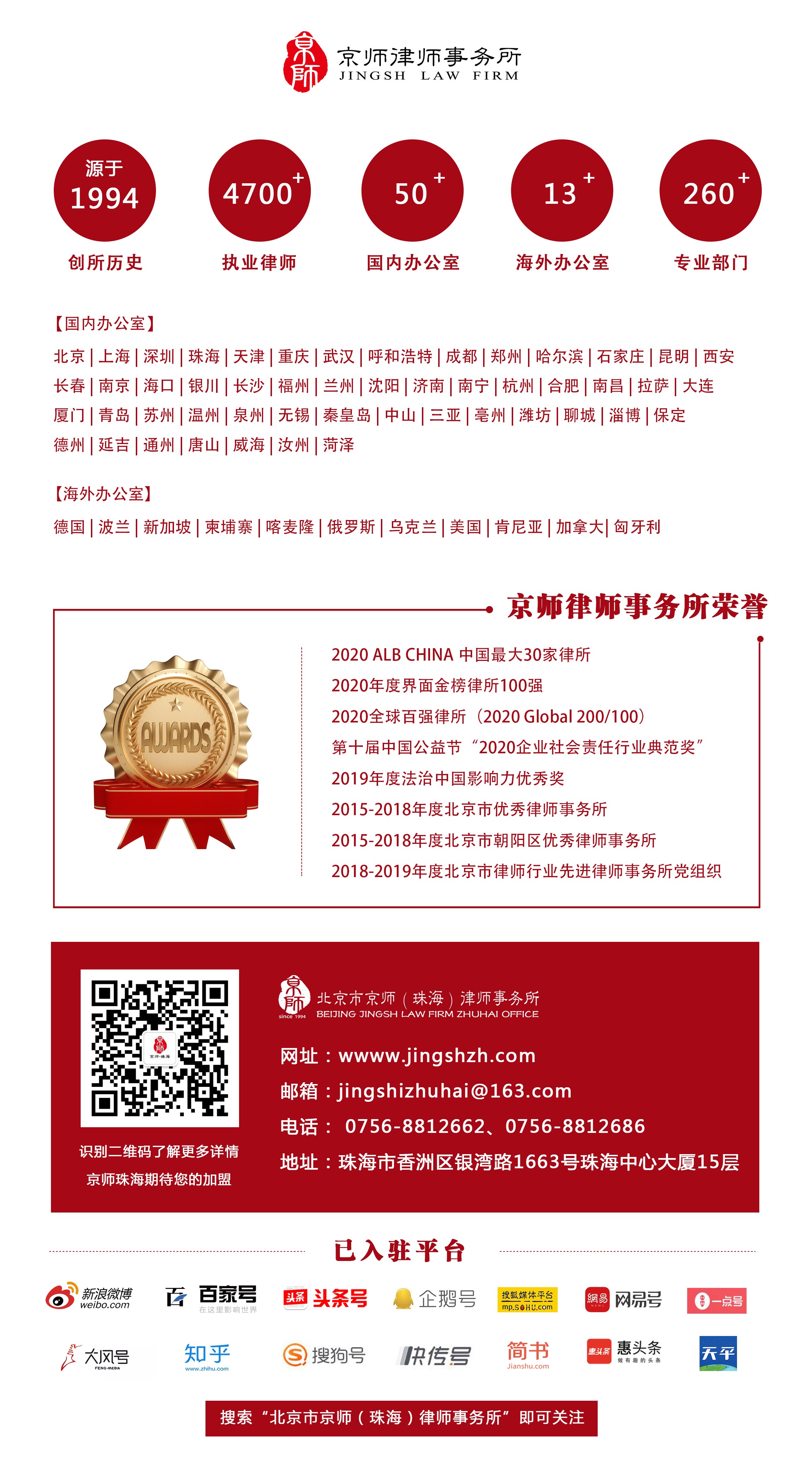引 言
现代公司制度下,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往往是分离的。在上市公司中,股东除了少数参与公司管理外,多数是社会上的不特定投资人,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与公司的高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空间和便利,容易使他们利用所掌握的信息优势以及控制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和众多投资人的利益。而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帮助股东了解自己投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有义务向自己的股东如实提供经营和财务会计报告。作为潜在的投资人,社会公众也更需要通过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来保障投资的准确性。所以,为了有效打击财务造假以及信息披露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司、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至此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正式加入证券、期货类犯罪家族中,并担任重要“角色”。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和日益活跃,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犯罪案件频发,该种类型的犯罪成为了证券、期货类犯罪中的重点打击对象。2020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四类资本市场犯罪加大了刑事惩戒力度,其中针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条文规定作出了重要调整:
1、加大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处罚力度;2、扩张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责任主体范围;3、进一步明确了单位犯罪。证监会在发文祝贺《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过时,曾总结此次修改对于资本市场犯罪的重大影响,其中就明确强调此次修改大幅提高了信息披露造假等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了违法犯罪成本,证监会下一步将着手推动加快修改完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会同公安部进一步健全行刑衔接机制、探索行刑深度融合协作模式,不断深化与司法机关协作配合、“零容忍”打击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推动完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本文通过最高检通报的典型案例,重点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追责主体展开分析。
一、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精准打击
2020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证监会召开以“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通报发布了12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华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被最高检总结为实现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精准打击的典型案例。
经查明,华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系上市公司)由王某家族控股,王某担任董事长,系实际控制人之一,多名亲属担任董事。为向家族集团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王某指使他人成立若干空壳公司,通过虚假业务向该家族集团公司提供资金。2013年末华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约8.2亿元,2014年末占用余额约11.5亿元,2015年6月末占用余额约13.3亿元。为掩盖关联方占用资金,王某安排员工将无效票据入账充当还款。
华某公司还以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为家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同时以华某公司名义为王某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3.35亿元。华某公司的相关定期报告未披露上述情况,同时相关定期报告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处理结果:2018年1月,证监会对华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市场禁入决定,认定华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监会决定,对华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王某处以90万元的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60万元;对其他责任人员分别处以3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款。同时,对王某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其他部分责任人员分别采取5年至10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责任主体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包括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负有直接责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监事等,即负责公司财会业务方面的主管人员。
需要强调的是,本罪系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是明知的,基于此,有两类人员不应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首先,在单位其他领导决定、指挥、组织实施的犯罪,而又不再本人职权分工范围内且不知情的情况下,该类人员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公司管理人员对于财务会计报告制假、造假情况并不知情,但由于其工作失误致使虚假财会报告提供出去的,也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直接责任人员”,是指直接参与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制作的工作人员,该类人员取决于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要求必须具有财会人员的身份。
本案中,王某既是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监会认定其主导、参与或指使他人实施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已经超出上市董事长职务行为的范畴,构成实际控制人实施的超出公司集合意志范畴的指使行为,依法对王某两种身份下的两个行为分别予以认定和处罚。证监会认定王某系“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自不必说,而对于王某以实际控制人身份指使财务造假的行为同样加以惩处,实现了对于“关键少数”的精准打击。
随着社会融资环境产生变化,有的上市公司长期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时有发生。有鉴于此,2019年12月28日通过的新《证券法》在“指使”行为的基础上,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信息披露违法或“隐瞒”导致信息披露违法发生的,也应承担相应违法责任。而最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也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施、组织或指使信息披露造假或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公司披露虚假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发生,故将此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进一步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追究。此举能够有效警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敬畏法律、敬畏规则,引导其肩负起规范发展的主体责任,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二、明确本罪中单位犯罪的认定
如前所述,《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追责范围仅限于单位“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并不追究嫌疑单位的刑事责任。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余蒂妮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检例第66号)被最高检总结为不予追究嫌疑单位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
公诉机关指控: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公司)原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名称:ST博元,股票代码:600656。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泰公司)为博元公司控股股东。在博元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有关人员作出了业绩承诺,在业绩不达标时需向博元公司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2011年4月,余蒂妮、陈杰、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等人采取循环转账等方式虚构华信泰公司已代全体股改义务人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3.84亿余元的事实,在博元公司临时报告、半年报中进行披露。
为掩盖以上虚假事实,余蒂妮、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采取将1000万元资金循环转账等方式,虚构用股改业绩承诺款购买37张面额共计3.47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在博元公司2011年的年报中进行披露。2012年至2014年,余蒂妮、张丽萍多次虚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交易事实,并根据虚假的交易事实进行记账,制作虚假的财务报表,虚增资产或者虚构利润均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或利润总额的30%以上,并在博元公司当年半年报、年报中披露。此外,博元公司还违规不披露博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公司等信息。
公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单位博元公司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主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以及其他人员的利益,情节严重。余蒂妮、陈杰作为博元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已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应当提起公诉。但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对博元公司依法不予起诉。
判决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余蒂妮、陈杰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余蒂妮等五人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宣判后,五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中,检察机关注意审查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内容,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正确区分刑事责任边界,准确把握追诉的对象和范围,对于嫌疑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于嫌疑单位本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是考虑到上市公司所涉及利益群体的复杂性、广泛性以及多元性,为避免众多中小股东利益遭受双重损害,即便将本罪追责主体扩大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但仍未将嫌疑单位纳入刑事追责范围,以此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但是,借助本案仍需强调的是,虽然嫌疑单位不是刑事追责的主体,却并不意味着本罪不存在单位犯罪。首先,就犯罪构成而言,法律条文将犯罪主体明确表述“依法负有信息披露的公司、企业”,彰显了本罪系单位犯罪,只不过与一般的单位犯罪不同,本罪实行单罚制,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刑事处罚。其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法律条文新增第四款作出明确规定:“犯前款罪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如果嫌疑单位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仍成立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
结 语
现代公司、企业法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地披露重大信息,对于提高市场定价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公司、企业管理秩序至为重要。然而,近年来频频爆出的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犯罪案件,相继暴露该类案件认定难、违法成本低等问题,财务造假和信息披露违法这一顽瘴痼疾,严重危害并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结合司法实践,明确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责任主体,将追责主体细化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公司的“关键少数”,做到精准打击,同时科学运用单位犯罪的单罚制和双罚制,有效加强信息披露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加大违法犯罪成本。此举不但能够有效惩治信息披露犯罪,而且对于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健有序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

■ 京师(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 证券、期货犯罪辩护研究中心研究员